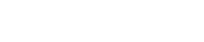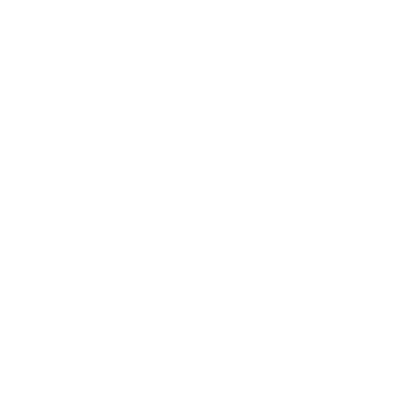撰文:馬迅榮(傳訊幹事)
今次我和同工出差尼泊爾,到訪該國南部和夥伴(Samari Utthan Sewa)見面,因為我們合作開展新的「預防及對抗人口販賣項目」,此行是要了解項目推行的進度。萬沒料到,期中一個行程竟然是到訪「夜總會」。
夜總會裏一片嘈雜,歌聲和伴奏大得我和同工要以大叫的聲線才可以交談。除了我們和同工,幾乎每一位客人都在吸煙,吞雲吐霧。客人走到台前,隨着音樂擺動身體,至於台上的舞者也不欺場,用力扭動腰肢,手舞足蹈。到一首歌終止時,歌手和舞者都會立即收起笑容,坐到一旁休息,然後等音樂再起,她們的笑容又會出現。
對我來說,那分明就是「對人歡笑背人愁」。這感覺可能帶點主觀,不過如果你也聽過這班尼泊爾的AES(Adult Entertainment Sector,下稱成人娛樂場所)從業員分享,你大概也會像我一樣「主觀」。
認識這班在成人娛樂場所工作的女孩,還有後來被她們邀請到夜總會「捧場」,都是一個下午之內發生的事。當日,我和同工在夥伴的安排下,於酒店與一些成人娛樂場所從業員見面。她們是施達和夥伴在2022年8月時開展的「預防及對抗人口販賣項目」的受助者。
在前往見面的路上,由於我不太掌握這個行業的情況,便不斷向夥伴提問,希望得到更多背景資料。據夥伴所說,成人娛樂場所並不是性交易場所,而是以歌舞表演為主,一旦涉及性交易就屬於違法。而將與我們見面的女孩是在合法的夜總會工作。
被剝削的一羣
或者你有疑問,既然有正當職業,為甚麼施達還要幫助她們?前來會面的女孩有八人,從她們的分享中,大家會得知她們是備受剝削的一羣:
一、人工低:她們每日由下午6時開始工作,一直到凌晨12時(甚至2時)。她們又跳又唱,每月收入最多10,000 尼泊爾盧比(即約港幣$600),而在市區一個午餐價格大約是500 尼泊爾盧比(即約港幣$30)。換言之,即使賺取最高人工,她們的收入也只能勉強應付食物的開銷;亦因收入微薄,於是有些女孩子會選擇提供性服務。
二、沒有保障:在見面的女孩之中有人負責跳舞,她們可能會受傷,但夜總會內連急救箱都沒有。一旦受傷或者生病,她們也不太想求醫,因為醫藥費可能佔她們月入的一半(會面時有一個女孩帶口罩,晚上跳舞時她也不斷咳嗽,看着就令人心酸)。
三、不公對待:其中一位女孩講述自身經歷,她曾被老闆意圖強姦,而即使有閉路電視片段作證,警方依然接受老闆的解釋:他飲醉時誤以為對方是妹妹,想抱她。另外,老闆也可能剋扣工資(甚至欠薪),而她們不會找到任何法律上的援助。

她們的待遇這麼差,為何還要每日向客人招手送笑,而不乾脆選擇離開,或轉投其他行業?這與她們的家庭背景有關。據她們自述,她們都生於農村家庭,父母會逼她們早婚,她們想反抗這種逼婚文化,所以唯有離開,如今已無家可歸。而因為家境清貧,她們都沒有機會接受教育,於是亦欠缺謀生技能。
「達利特」羣體
那些女孩在農村家庭長大,如果同時又是「達利特」(Dalit,又稱「賤民」,種姓制度中最低層)的話,就要承受更多的壓逼。據夥伴調查所得,八成成人娛樂場所從業員都是來自「達利特」家庭。因為在尼泊爾種姓制度已經廢除,但「達利特」在文化上仍然遭受歧視,例如他們就算被「非賤民」性侵、打死,案件都可以不了了之;經濟上他們也被逼從事低下的工作,例如清潔工,而就算做小生意也有人不願意跟他們合作。他們的工作和教育機會往往比「非賤民」差。我們當日所見的八個女孩中,有六名就是出身「達利特」家庭,有人自述和「非賤民」結婚,結果被對方家人厭棄。
在成人娛樂場所打工,可以是環境所逼;不過我們也無法排除有人喜歡表演,同時又可以賺錢,於是自願留下。傾談到最後,有女孩表示想離開這個行業,只是沒有方法;也有人表示想繼續,但希望有尊嚴地工作。

離開時的期望
面對她們這些需要,施達和當地夥伴計劃以不同途徑,改善她們的生活和工作環境,例如:成立從業員網絡,向僱主提倡僱員的權益,並提供職業訓練令她們有其他謀生技能。透過這個事工,我們希望令這些女孩能夠在安全環境之下工作,同時也有選擇離開這個行業的自由;更加希望使「達利特」羣體的權益受保障,在工作上得到公平的待遇。
這個項目在8月開始,如今從業員網絡已經成立,不過她們能否集合同業的聲音,組成一個強而有力的羣體,以致向僱主爭取權益還是未知之數。因為她們分享,某些同業認為她們在搗亂、是「害羣之馬」。
離開夜總會,那些女孩下午所流的眼淚,和台上的笑容在我腦海交疊。那裏明明應該是娛樂場所,但我和同工的心情都不快樂。因為經過下午的傾談,我們已經感覺像朋友一樣,她們還邀請我們去捧場;看見朋友要對人歡笑背人愁,怎麼可能覺得快樂?我祈禱,希望這些女孩面前的路能夠平坦一點,在不久將來可以有尊嚴、快樂地生活。
今期《呼聲》目錄
撰文:馬迅榮(傳訊幹事) 今次我和同工出差尼泊爾,到訪該國南部和夥伴(Samari Utthan Sewa)見面,因為我們合作開展新的「預防及對抗人口販賣項目」,此行是要了解項目推行的進度。萬沒料到,期中一個行程竟然是到訪「夜總會」。 …
撰文:馬迅榮(傳訊幹事) 2022年11月,第27屆聯合國氣候峰會在埃及舉行。會上,來自尼泊爾的24歲青年什雷雅 (Shreya KC)發言 :「我們活在被冰川融水淹沒的恐懼中。」為甚麼她會這樣說呢?氣候峰會和尼泊爾冰川有甚麼關係? 原…
Previous Next 災害下的兒童 水災、旱災、熱浪……當成年人面對各種天災時也措手不及,我們可以想像到,面對災難時,兒童的身、心、靈會遭受多大的傷害。 與成年人相比,兒童的身體機能發展未及成熟,災害對他們的影響會更嚴重。當災難影…
撰文: 趙汝圖 耶和華說:以色列啊,你若回來歸向我,若從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,你就不被遷移。 你必憑誠實、公平、公義,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;列國必因耶和華稱自己為有福,也必因他誇耀。 耶和華對猶大和耶路撒冷人如此說:要開墾你們的荒地,…